我觉得这个主题特别重要的两个词:一个是“传承”,一个是“互鉴”。传承方面,我觉得岳麓书院本身是一个中国文化传承的典范,因为它是一个一千多年前已经存在的书院,到现在还继续在新的形势下存在、发展,这就是传承的典范。这样的例子在全国不能说绝无仅有,反正是很少。现在,大家都已经意识到传承文化的重要性,我们国家领导人也提出了两创的思想,但是,如何传承或者哪些结构性的传承体系需要建立?我觉得现在还在探索。我们知道大学是传承传统文化很好的机构,但是如何使书院,甚至更多的民间书院发挥在传承传统文化中的作用,目前都是在各自自发探索的过程中,我认为需要一些经验性或机制性的肯定。传承其实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自信的问题。近代以来,有一些人认为中国文化断裂了,一个很重要的表征是文化自信消失了,大家认为传统对日常生活没有多少用处了,甚至是束缚人的自由和个性的,就没有必要去传承了。我认为这一点要通过大家切身的体会来认识到传统文化不仅有作用,而且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还可以发挥特别突出的作用。这样,文化自信才不至于成为一个口号,而是成为大家的共识。
主题词中“互鉴”这个说法我觉得也是特别好,因为文化自信的消失这一现象首先是在互鉴中产生的。近代以来,西方强势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压制,导致我们在跟西方文明做比较的过程中失去了自信。因为我们逊色于西方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所以我们逐渐的放弃了互鉴,变成单方面的借鉴,按照当时很多人的情绪化的说法,要把自己的书都烧掉或者扔掉,以实现全盘的、充分的世界化,充分的去吸收西方的文明。我觉得这个是近代以来文化比较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这种现象。近几十年,我们又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或者说通过自己的经济的复苏、发展、自我纠正,再学习西方过程中不断的成长、强大,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所以我们逐渐从那些文化的失落、迷茫中走过来,重建起信心。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就是重建自信的阶段,而且才只是一个开始。在这个开始阶段,我们真正开始了互鉴,我们一方面认为自己要向西方或者其他文明学习;另一方面,我们也认为自己的文明中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因为只有有了一定的文化自信,才可以谈得上文明互鉴,否则就只能是一个单方面的吸取。所以,像国学大典这样的活动,它更多的是给人们传达出我们文化自信开始恢复的态度,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互鉴。这是我对这个主题的看法。
凤凰网文化:干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的恢复建立在对传统的传承和理解的基础之上。您也提到书院,其实从过去书院到现在的这样一种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跟科举的取消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们整个教育制度发生的改变,包括现在岳麓书院虽然也是以传承传统文化为己任,但也是基于在这样一个现代学科体制下。您认为如何能够把传统文化的教育推广到一个更广的阶段,而不是仅仅在大学中几个非常小的学科的这样一种体系之上?
干春松: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首先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两办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在全国的中小学里面推广传统文化的教育。到了大学阶段,某种程度上说有点晚了,对传统文化的一些重要内容的亲近感其实是要从小进行培养的。这个培养其实也不完全是靠政府的推动,而是很多的家长会主动让孩子去学习传统的典籍。这一过程为什么会变成一个上下配合?一方面是政策的支持;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家长主动的让自己的孩子学习书法、民族乐器。这就造成了一个共同的力量,这个力量从我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研究者来讲,是感到特别欣慰的一件事情。在设计课程方面,我参加过一两次教育部对于中小学里面怎么传授传统文化的规划和讨论。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做法是挺好的,比方说在语文课或者说历史课里面更多的加入一些古典文学的因素或者古代历史的因素。还有一些做法我也觉得值得肯定,就是加强中国古代科学发明或者古代艺术发展的历史教育。这样有一些潜移默化对学生产生影响,学生上了大学以后可能仍会继续维持或者发展这些兴趣。如果仅仅依靠岳麓书院或者大学里面的文史哲的专业来传承传统文化肯定是不够的。
我觉得现在中国几个比较著名的学校,如北大、清华、复旦都有一些通识课程。清华现在也开始恢复了某种意义上的书院制,虽然跟古代的书院不一样,但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就是希望在大学分科教育的基础上提供一些通识性的内容。其实北大也有这样的课程,我自己也在北大开通识课,选课的人员几乎涵盖所有院系。这一过程,开始让传统文化在整个学术体系里中有了应有的地位。我觉得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的确是“礼失而求诸野”,很多从海外回来的人反而能意识到古代经典对于个人培养的重要性。因为西方那些最著名的大学无一例外的忠实于他们的传统文化教育,重视古代的经典在现代教育体系里的作用。所以,我觉得以后再发展下去,应该会出现大家更充分的意识到传统经典对个人整体视野的建立和价值观建立的重要性,所以我自己还是很乐观的。我认为传统文化真正的复兴,不是在不同的学校里复制岳麓书院这样的建制,而是探索如何在现代的教育体系里让这些经典的力量重新焕发出来。关在一个小院子里面闷着头学习古典文献当然是需要的,只是针对少数专才。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讲,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通过经典的阅读和这些伟大人物的人格熏染,意识到自己跟传统之间的关联性。
凤凰网文化:您作为本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的国学成果奖得主,您的学术生涯一路走来肯定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您觉得有哪些人或者哪些书、哪些事情对您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什么?
干春松:刚才我说了,推荐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避免自吹自擂,因为自己申报要讲我这个成果如何如何重要。但是,既然有这么一个环节,我也只要“自我表扬”一下。我也写过一些文章,以前包括《南方周末》的“秘密书架”专栏写过自己的读书心得。我其实也梳理过自己成长经历中的这些老师对我的影响。在80年代上本科的时候,受两位学者的影响特别大,让我决定后面从事我现在在做的中国哲学的研究。一个是李泽厚先生,其实我在80年代只是听过他的讲座,不是很认识他,但是那个时候,正好他的《近代思想史论》、《古代思想史论》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这三论出版。尤其是《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让我看了很惊讶,古代思想史居然可以用这么优美的文笔,这么有趣的方式呈现出来,完全没有距离感。像老子、庄子、孔子这样的一些人,李泽厚的写法跟别人不太一样,他不是考据式的写法,是一些观念性的讨论。这些观念性的讨论是跟他所处时代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摆脱了很多唯物、唯心机械的讨论,给人以阅读上的快感。后来有意思的是,李泽厚先生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在三联书店出“李泽厚作品集”的时候,腰封上引了我一段话,强调了李先生的书对我的阅读的快感。我觉得文字表达方式是传统文化在以后研究和传播过程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我们读冯友兰先生的书、李泽厚先生的书都是这样,许多非专业的读者都觉得很有阅读的兴趣。这个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个就是方立天老师,人民大学的一个研究佛教的教授。他给我们本科生开中国哲学史,他给我们开哲学史的时候,他已经很有名了,是教育部特批的几个全国仅有的几个从讲师直接升到教授的学者。倒不是因为他的名头让我们要追随他,而是他上课的方式,方老师上课的方式是娓娓道来,所有的结论和他的论据都是衔接得特别好。尤其是他给我们讲佛教的部分,因为他的特别专长是研究佛教,佛学是必须艰涩的。我印象特别深,他讲僧肇的“不真空论”,我觉得讲得特别透,我印象特别深。这样以后,等到本科毕业要选择考研究生考什么方向的时候,我觉得一方面我对自己的文笔有信心,我觉得我未来应该能写出很流畅的文字。第二就是因为方先生和李泽厚先生让我们觉得这些古代的东西它不是一些遥远的过去,而是随时可以从那里获得思维上的启迪。当然,跟我们同时的很多人可能是喜欢考西方哲学,那也挺好的,但是从我个人的生活或者说学习的倾向来讲,读老子、庄子、孔子这些东西让我更有亲近感。所以,有了这两个先生的启示,我确定了我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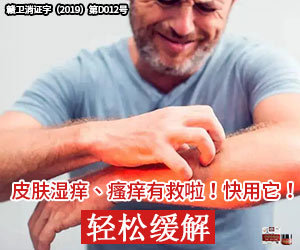
进入二十一世纪了,我才有机会与李泽厚先生面对面的交流。一方面年少时候对他的这些敬仰终于在跟他交流的过程中,得到了某种程度心理上的满足。第二,我觉得他依然是一个让我特别佩服的人,他现在已经90多岁了,但是他始终没有停止思考,他一直在写文章。这其实是一种人格上的震撼,就是有一些事情是可以终身行之的,比如终身的学习、终身的探索,学无止境。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思想的吸引力,会让人觉得这件事情可以一辈子干下去,这是一件特别愉快的事情。
